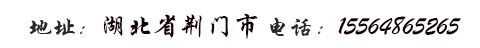芥子须弥,微尘三千
|
亦是一个不完全镇定的深夜。面对缓缓滚动的VisualStudio下载进程,我突然毫无预兆的痛哭起来。甚至只敢略高于呜咽略低于啜泣的崩溃,因为门外还有安然平静的熟睡的父母。 我觉得痛苦。并非单单是来自考研的复习压力或是专业课上繁忙芜杂的实验与原理,是近来纷纷扰扰各式各样的从社会到人群一股脑涌现而入的烦恼与思考不停地纠缠着我,包笼着我。我为之做过很多突破,去尝试新的爱好,新的朋友,新的地点;也去和旧的爱好,旧的朋友,旧的地点,做出很大程度上的让步与和解。可是这次宏大的心愿并未如愿以偿,相反的,我不断地又陷入更多日常的缝隙中难以自拔。譬如我驾驶一度将笔记做到极致,在白天感觉自己就像个录像带与AI机器,做的动作几近一致乃至复刻。教练对我时常充满自信,他很少批评我,在得知我的心态差异后还多次安慰鼓舞我。纵然如此,焦虑尚且不增改一分一毫的缓和。我最后明明白白,我根本不是在和驾驶科目做对抗,我在和自己且深深地和自己做对抗。直至我的教练离开了岗位,我都难以从这次失败中抽出一点点轻松。 譬如,我很难接受“失去”。在这个疫情假期中,让我变脆弱很多。每一天每一秒的逝去开始让我过度紧张,我拿出了我许久没戴过的手表,听见指针转动的声音会让我多多少少舒缓一点点。因为有比时间走过更多、更大的失去,让我无能为力。小倏走之前的那个夜晚,我其实早有预感。这可能并不是具体到某个人、某件事,是一种宏观的到来——我觉得会有一场强有力的冲突卷席我的立场。事实证明,果真如此。最近这种虚脱感越来越强烈,经常会有一种乍然的刺痛戳入我的骨髓。在这种反常的动态驱动下,我通过抠捏茶叶杆子降低自己的不安感。白天不能走熟悉的路,想说过的话,不然就会经历一段持续的震颤。这是一种危险的标志,我觉察到并且试图在解决之。这样的事情让我偶尔产生错觉,似乎自己一直站在波涛汹涌的海水面前,面前是一片蓝,纯净的蓝,淹没、吞噬我的身边物质。断断续续带走让我支撑下去的若干情感与热情。 一旦说到痛苦,好像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就像说起意义这个词,似乎也不是很有意义的样子。人类往往在从一个痛苦奔赴另一个痛苦,在痛苦中和痛苦过来回切换。失眠困扰着我,而打游戏显然并不能促使我快速入眠。正如此,我恍惚感觉,人生来的的确确是被痛苦包围着的。想起小学,最常写的词一个是高兴,一个是开心——这很微妙,因为人类需要无数个平衡,无论这是否被人为定义,因为会在将来意识到N个痛苦,所以在享受不到痛苦的年龄大肆渲染非痛苦的说辞。就如同这个世代愿意把佛系挂在嘴边,因为大家每日的生活相对更生死时速一样。痛苦的本源是什么?痛苦会从哪里来?痛苦是有害的吗?痛苦是我们自我生造的吗?这突然需要我们向这个词的定义发问;而在发问之前,我们又面对其他一些待重新斟酌的事物:意义与对错。在交流上人与人都会有沟通的困惑,而在宇宙内正是无穷无尽个物质与物质的对话(无论是否为人类学的范畴)组合而成的;那么世间万物应该怎么接受与认同一种意义?约定俗成的意义?到底什么样的意义才叫做意义?什么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事情到底有怎样的意义?意义是人赋予的,那人赋予的就有他应该有的意义吗?人未曾赋予的呢?如果做了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它就是不正确的吗?或者,如果大家认为不对,大家就对了吗?到底应该用何种方式,去让一个人,你我,任何谁,能够坚定,天地洪荒,这样做有其合理的方式。真理是否为真,为我想的那个真,我想的真是否为真,真是什么,什么是真?倏对我说,学工科的,应该有一种思维方式,就是精确度。而我想,我从我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里面感触最深的,也是信号的失真。经过信道的推送,困惑度是一个毫不避忌的指标。大学至真,这个真,真让我为之动容。 经历了很多后,表达爱的方式都含蓄了很多,收敛了很多。同样,恨也是。现在,在我无法恰当处理好我对任何事物的态度之时,我就会下狠心,远离之。这也是我能想的出来对彼此最好的交代与保护了。我是一个触感格外敏锐,痛感往往延迟触发很久的人。我并不想把这份罹难传导给身边的谁与谁,不管我是否还爱着他/她。这是我命令给我自己的责任,是对所有爱过我、还爱着我的全体成员的不辜负。当你不会爱一个人的时候,接近就是一种伤害;当你接近一个人的时候,离开就是一种伤害;当你离开一个人的时候,遗忘就是一种伤害。我可能也无可避免的做出伤害别人的举动,别人也是。如同这个深夜,别人也会在台灯前,情难自己的哭出声来。 你我相遇的意义最终为了离别,酣畅之片刻最终为了草率分篇。放弃不代表完全彻底的失去,获得也只是某一时局下的胜利。 诸相皆不为真。大盈若冲,大成若缺。芥子须弥,微尘三千。清尘浊水,濡沫涸辙。 天生牙zrl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ezia.com/jztz/5605.html
- 上一篇文章: 独家过年好票房难过亿,导演高群书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